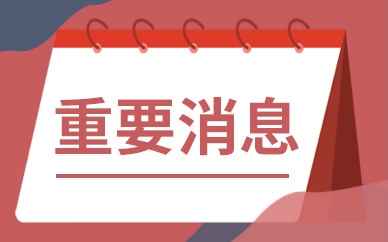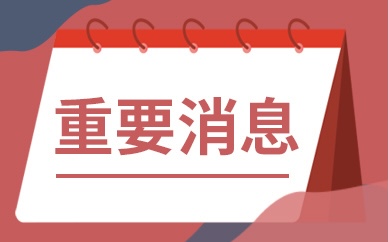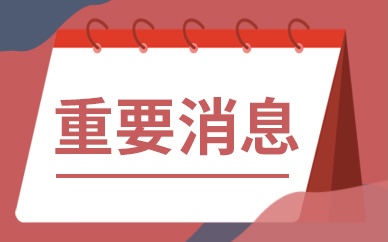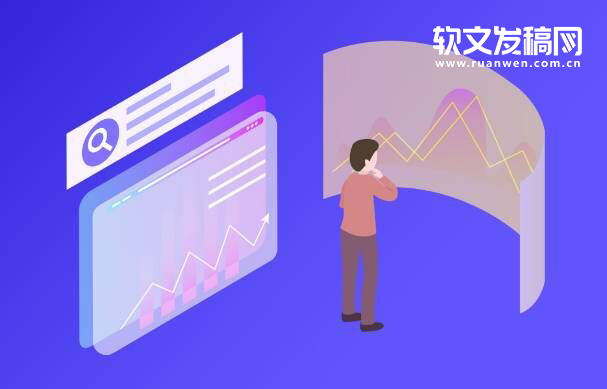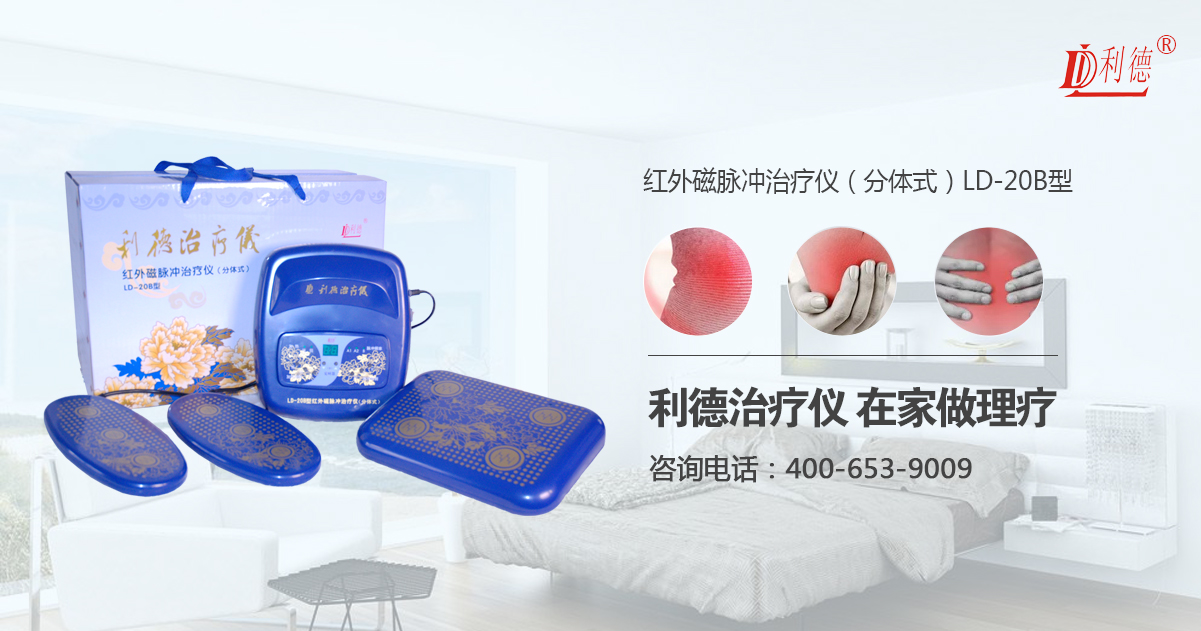第二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七个老人八颗牙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文/恨铁
一
“咯咯!噗噗。”对门山上的那只野鸡又开始闹了,扯起嗓子叫两声,再拍两次翅膀。每天如此,似乎老天是被它喊亮的。
“这两坨嫌脸肉哦,怎么就这么讨厌唦!去去去,我又不是狗母娘!嗯——”每天这个时辰,母亲都会用这样的开场白与野鸡呼应一回。母亲真真假假骂的“两坨嫌脸肉”,是天天听见响动就会跳过来守在门外,摇头摆尾等着开门的两条狗子。
母亲的语气本来怪有味,但最后拖出的那声长长的“嗯——”,让味道转眼所剩无几。我曾试探着问:妈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她却转脸笑了:没有啊。我继续问:那叹什么气啊?她不好意思地抿抿嘴:想叹就叹呗,又不花钱;要么矢口否认:我叹气了?
母亲走出卧房时,鞋子都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穿过堂屋去开大门时,会拖出一路的嚓嚓嚓,地上都快拖出两条槽来。又不是穿着拖鞋,我小时候要是这样拖着走的话,母亲肯定会责备一句:鞋底不烂了吗?想起当初的情景,我几多想劝母亲把脚步抬高一些,但每回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母亲打开大门时,会弄出一阵更大的声响,嘎嘎——咔咔——。垮山似的,那是不锈钢大门与瓷地板砖刮出来的,刺耳挖心。乡下的泥瓦匠就那水平,那么平整的地板砖,都要被他们铺得这边翘一点那边低几分,还要把责任推给地基:新修的房子都会下沉三年。我本有一箩筐的理由反驳,按此说法,那些快要戳到神仙的高楼,得下沉到什么样子?但我懒得浪费口舌,因为母亲也宁愿帮泥瓦匠说话:“人家不是怕老鼠钻进来才把缝隙留窄一点的吗?你还不领情。要是门板和地板砖有一样不那么硬,不是几天就磨平了?”
母亲以前打开房门时,冲过来的狗子是一条。那条狗子养了十五年,母亲或许真愿意把它当儿子了,可最终还是被某位遭天火烧的家伙偷了。母亲不骂偷狗者,骂公路。以前公路不通的时候,我们山里日夜不关门也一万个放心,公路一通,还打成了水泥路,那些满口“叼腔”的远方人,都苍蝇一样赶过来了。卖砧板菜刀的,卖锅盘碗盏的,卖锄头镰刀的,卖被子毛巾的;收破铜烂铁的,收土鸡肉鸭的,收生猪山羊的,收狗子的……甚至还有名正言顺“积德行善”的。几个月前,就有几位噼噼啪啪开着三轮车,一副争做党的好儿女的样子,口口声声为山区百姓送惠农政策来了。谁把旧的碾米机给他们,再加一百元跑路的油料钱,三天后他们就会换一台新的送过来。你不相信他们都不好意思。人家的三轮车上拉着“新农村建设便民服务队”的红幅标语,随车的喇叭喊得山响,还拿着红头文件,还有“委托书”让你签字认可,还有办公室联系电话。你躲到某个旮旯里打个电话过去,还没开口人家就是一声“您好,这里是县农机化惠农公司……”其实,电话铃声就伴着音乐在告诉你,他们来自哪里、是干什么的,还欢迎您上门咨询,连门牌号码都说得一清二楚。嘻嘻哈哈间,母亲成了第一个响应者。别人也一边羡慕一边想跟着母亲沾一次光,但人家一脸歉意:这回每村只有一个指标,等下回有了新政策,一定优先考虑提前登记在册者。
几天后不见动静,再打电话,没人接。再打电话,停机了。再打,空号。
明白上当后,西头的邻居坤叔、东头的小婶、北边的毛陀再次围拢来,一边分析千万种可能,一边帮母亲出气:这些剁八块的,怎么就演得那么真啊?让他们生个孩子都不长屁眼!母亲却一笑了之:“冤有头债有主,咒人家的孩子干什么?不就是几百块钱吗?退财免灾,就当我抓药吃了!”一调头,母亲甚至反过来为骗子担心:“总有穿帮的日子吧?如果哪天在别的地方穿帮,要么被打断胳膊大腿,要么被抓去坐牢,我看谁帮他们养家糊口?”
我有些无可奈何:“妈,你是观音菩萨转世吧?”
母亲笑眯眯地反问:“有几个日子好过的人愿意冒险当骗子、偷狗子?”
母亲的心思又跳到那条狗子身上,甚至已经估摸到是哪个家伙偷走的。那个穿红衣戴头盔的中年男人,骑着摩托飙来飙去的时候,母亲正在稻场边择菜。那家伙还和母亲对望过一眼。要不是匡着封闭式头盔,下次遇见肯定能认出来。狗子那天也是阳世日子满了,摩托屁屁屁把房前屋后都震得摇摇晃晃,它却一声没吭。当然,或许是摩托天天找魂一样到处窜,狗子也见怪不怪了,加上它也老天趴地了,懒得起身。那家伙杀过去没多久,母亲唤狗子吃饭,半天不见动静。找来找去,最后在狗窝旁边捡到一支麻醉针。母亲愣着眼一言不发那会儿,坤叔也赶过来帮母亲描述起偷狗子的过程:那些家伙带着一根一两尺长的不锈钢管,比大拇指粗一点,将麻醉针倒插进管子一头,管子另一头含在嘴里,鼓起两腮一口吹出去,麻醉针比梭标还快,扎在狗子身上,成了。比有些家伙在女孩的茶杯里动手脚还来得快。
“哎哟,不会是你干的吧?”尽管母亲觉得坤叔最后的比方打得有些不对味,但终究不愿再郁闷下去,甚至马上把话头引向别处:“真有那么厉害的话,我几时也去买几根。每年的黄豆地里兔子成灾,射中了还有肉吃。嗯——”哪怕同样拖着一声叹息,但母亲仿佛成了百发百中的猎人。
“有个办法应该起效。”坤叔说。
“多养几条!那些家伙再厉害也不可能一针射几条。只要动手,几条狗子肯定一起上,不把他撕成肉条算他命大!”母亲这会儿的脑子出奇地好使。
“我还以为你没想到呢!”坤叔也对母亲佩服得五体投地。
母亲养了两条狗子后,果真起了效。连坤叔、小婶、毛陀也纷纷效仿。四户人家八条狗子,有人打个饱嗝,畜生们都会一呼百应齐上阵。连经常走村串户的“叼腔”佬,如今也少了许多。
有了这两条狗子,有人再提起被偷去的那条老狗子时,母亲的想法已经变得让人跟不上节奏:“被偷去了也好。电视上说狗子活一岁相当于人活七岁半,它等于活了一百多岁,还能活几天?要是不被偷,死了我还得收埋,弄不好更堵心。”
赶开两条死皮赖脸的狗子,母亲脚下的嚓嚓声渐行渐远。转眼,房子东头的小院里,响起了又一阵清脆的热闹声:
“你们这些剁辣椒炸的!怎么就这么不明白呢?鸡窝明明是生蛋的,你们偏要在里面拉屎!再不听话,我不给你们胀的,看你们还拿什么拉?嗯——”
母亲这会儿责备的,是小院子里的那群鸡。
二
“什么时候回来的?”坤叔问我。
坤叔也是踩着野鸡的嗓门出发的。虽然是邻居,但离我家也有大几百米。此时,他一手握着牛绳,一手托着旱烟斗,吧嗒一口,一步一顿,不紧不慢从我家屋山头经过。本可以从自家门口直接赶牛上山,可坤叔宁愿绕个圈,直到把圈差不多绕对口时才再上正路。绕一大圈废路,似乎就为了找段相对平缓的领地多吸几口烟。一口口浓浓的烟雾,都要飘出一路仙境了;叮叮当当的牛铃声,宛如压着野鸡的号角唱出的歌谣。这也是催促山野快点睁眼看世界的定时钟。
“昨天晚上回来的。您这么早啊,来,抽烟。”我多少有些讨好卖乖。毕竟,我的香烟比坤叔的高一些档次。坤叔有时接有时不接。接过去的时候也不会抽,轻轻托在手心里晃一眼,趁我不注意时当宝贝一样放进口袋;不接的时候,一句“你抽你抽,纸烟香是香,就是不杀瘾”。不管接不接,坤叔都是一脸的兴奋,两排黑黑的门牙比玛瑙还光亮。我猜想,坤叔的兴奋大概从看见我时就已经在探头探脑。问我什么时候回来那会儿,双眼已经流光溢彩。其实,自从三年前把老屋翻修后,我每个周末都必回乡下。坤叔的问话,也就是见了面随口表示个礼节而已。
每个周末的早上,我都会紧跟母亲双脚拖地的声音翻身下床。蹲在稻场边,一支接一支地烧烟,似乎要把一晚上的损失补回来,抑或静心等待某个人的响应,坤叔,或者和我同辈的毛陀。如果一时半会儿等不来,我便绕着房子转来转去。那里有我随处可见的“成就感”。房子建起时,房前屋后杂乱无章,这里一堆土那里一片草,请人来干腰包又不充实,我便自己动手。一开始,多少还有些“被干活”的感觉,但人往往就是贱骨头,干着干着似乎还找到某种乐趣。就像许多原本没有感情的夫妻,一旦拖儿带女后,也便甘愿死心塌地守一辈子。我一年四季待在城里,横草不沾直草不拿,曾装模作样搞锻炼,可身体依然像发馒头。从回老家翻修老屋开始,锻炼不搞了,也就每个周末不紧不慢磨两天洋工,滚圆的肚子居然不知不觉瘪了下去,浑身钻来钻去的那点酸痛都很享受——只有体验过的人才能明白。直到现在,酸痛都不见了。老婆甚至死皮赖脸地说,我交作业的质量都提高了好多。
两三年下来,屋后原来紧贴屋阳沟的一大方黄土不见了,让我一锄一筐开出了一条三四米宽的通道。坤叔和毛陀都抢着给我计算过工程量。坤叔说:铁子,我随便算了一下,你至少运走了五六七八十上百方土,真是个狠人。毛陀觉得这账算得有味道没水平:坤叔你这也叫算账?究竟是多少啊?说完,他干脆扯开脚步去丈量。按乡下的老办法,六步一丈,连半步都算出尺寸,再一米三尺十米三丈,只差精确到小数点了,再长乘宽乘高。算得坤叔满脸愧疚,算得我也干劲十足。接下来,我又开始满山遍野锤石头,一锤下去石头抖都不抖一下,换个地方再一锤下去、两锤下去,一钢钎下去、几钢钎下去,或许就是一块、一堆。再一块、一堆铆足力气搬运,搬不动就一步一摇地翻滚。哪怕有时眼珠子都要铆成牛卵子了,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真有其乐无穷的时候。再过些时日,一道一人多高的石墙拔地而起。石墙紧贴通道一边的土墈,像一排死死挡住黄土的卫兵。屋后那条通道也因此变得整整齐齐。坤叔和毛陀又帮我算账,但不再算石方了。算钱。坤叔说,要是请人干,没得大几百成千上万块钱能行?这样的算法,再次让毛陀抓住了辫子:“坤叔啊坤叔,你哪天才能说个准确话?”
坤叔和毛陀的一阵嘴皮子,让小婶也跟着好一阵乐呵:
“我看铁子当初就不该跑出去吃国家饭!是不是不干活骨头就痒啊?”
只有母亲从不评价一句。我猜想她是很乐意的,她甚至动不动在石墙边眉开眼喜,但只要发现我,就会拖着那声习以为常的“嗯——”,摇摇晃晃离开。
大伙围绕那条通道乐呵来乐呵去,最后居然惭愧起来。坤叔一脸愧色拿自己跟我比:“全天下我只看到铁子!要是我们都像他,这四周八围的山恐怕都要矮一大截,卖石头土块都能当万元户,年轻人哪还需要出门去打工?”
“万元户?”毛陀嘻嘻哈哈摇着头:“坤叔啊坤叔,听你说话我脑壳就胀得生疼,现在当万元户还有个卵用!”
坤叔这会儿确实没说到点子上。但坤叔不服:
“哎呀,你怎么就那么喜欢钻牛角尖啊?我就是打内心佩服铁子嘛。”
“哈哈,我晓得,我也佩服。可……”
毛陀终于找不到下句了。坤叔总算占了回上风。
越扯越远了。但我知道,他们对我的佩服实在有些夸张。真要想一想,怎么会是他们佩服我呢?我最多也就是过腻了城里的日子,想利用周末调调胃口。再远点说,也就是觉得十来年后,有个可以回老家居住的理由。可他们呢?就说坤叔,老婆的脑子天生就有问题,还常年一身疾病。夫妻俩一辈子生养了三个儿子,两个大的还是双胞胎,但他们一同接下了母亲的衣钵,甚至“出于蓝而胜于蓝”。都年近半百了,三天两头还把大小便拉在裤裆里;小儿子倒是聪明得一个脑袋赶上别人几个,但年近不惑还家都没成。这世上,即使什么都不缺的男人,不找个女人搭伙,日子也只能三日不滚三日不冷。坤叔的小儿子以前在外打过工,还带过一位女人回家。但一夜过去,女人哪里来的转身就回哪里去了,把坤叔的小儿子出门打工的理由也带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就算捞一座金山,没人帮我看管又有什么意思?
谁的心里都明白,小儿子的日子是受了两个哥哥的拖累,只是谁都不说。说了也不管用。真要说的话,坤叔又有什么盼头?可他依然像头绕着米碾停不了脚步的老黄牛。
山里田地不多,以往搞大集体时,村民们就常年靠救济粮、返销粮熬粥喝汤,整个村子也因此只有二十多户百多口人。为此,方圆十里还流传过一段顺口溜:金仙阳、银渡水,孙家村里出穷鬼。好在二十多年前开始,能往外跑的都可以想跑多远就跑多远,如今留在家里的,一口气可以数几个来回。山里的田地也随之成了多余。留在家里的大都是老者。像毛陀、坤叔的小儿子这样,四十来岁还愿意守在山里的已经凤毛麟角,即使守在家里也不栽田。毛陀专门养猪,坤叔的儿子想干就干不干就玩。毛陀养猪倒是不错,年年出栏大几十头,栽一亩田赶不上养一头猪。老人中有想栽田栽不动的,也有根本不想栽的,田地也便扔抹布一样东一块西一片。坤叔这些年的日子,就是到处收别人的田地耕种。向阳地带的,灌溉方便的,用坤叔自己的算法,少说也有八九十几二十亩。这回算账连毛陀也找不出毛病,零星的田地谁也懒得去丈量,当初分田到户时都是眼一望嘴一张,这丘那丘一对比就算数,如今就更没必要弄清确切面积了。散落在山中的田地,得靠犁耙耕牛翻耕,靠镰刀板桶收割,靠箩筐扁担压得背躬腰驮,但坤叔义无反顾。连母亲也不止一次告诉我:你坤叔说他只喜欢夏天。夏天的白天长,每天可以多干好几个小时。不像冬天,眼皮还没撑开又要闭上。母亲唠叨这些时,似乎都有些心酸,可每遇别人劝坤叔少栽几亩田地时,他总是笑眯眯的,嘴角都快拉到后颈窝:
“祖宗八代都想多几亩田地,到我手里终于如愿了!哪有留着地主不当的道理?”
不过,我从心底觉着,坤叔“愿当地主”的说法也就是过过嘴瘾。
“我真希望两个大东西早点走,要是走在我后面,谁来照看他们?”
大概就是这种心思,坤叔两年前开始连粮食都不卖了。他每年可以收两万来斤稻子,一家五口需要吃五千来斤——尽管这样的人均口粮有些不可思议,但这不能怪坤叔。坤叔一天吃一升(约两斤)大米,那是换力气的,类似于给发动机加油。浪费的粮食应该算在老婆和两个傻儿子身上,他们恨不得一天到晚吃,每顿都得逼他们放碗筷,放下碗筷还得闹一阵。剩下的一万五千来斤怎么办?早些年变卖,换日常开销。两年前开始,日常的油盐钱有政府给的低保,低保户连患个小病也免费;坤叔和老婆每人每月还有五十五元基本养老金。积攒得法的话,坤叔每月还可以有几张捏出一手汗的毛票。坤叔把吃不完的稻子全部储藏起来,转眼已经储了三万斤。坤叔的目标是十万斤。坤叔找先生算过命,自己有八十岁的“阳寿”,还剩九年;坤叔的老婆比他的“阳寿”要短,肯定走在坤叔前面;两个双胞胎傻儿子,今年刚吃五十岁的饭,算命先生把他们的“八字”排到七十岁就不说话了。坤叔明白了。再不会算账的坤叔,这回一个大概加估计,也算出了连毛陀都愣着眼不再否定的一笔账:自己离八十岁还有九年,储藏到十万斤稻子时还远远不到八十,还可以轻松好几年。十万斤粮食,坤叔八十岁之后应该还剩下好几万斤,傻儿子们再怎么也可以吃到七十岁。
当然,保管十万斤粮食不是件简单事。现在才三万斤,坤叔就恼火透了。十口木板仓靠墙立着,四间土屋间间都变窄了一尺多,已经成了一道风景。只是,坤叔储着那么多稻谷,平日里食用的米饭却形同嚼蜡。因为不是新米饭。害怕稻子放久了变质,坤叔每年都要吃陈粮储新粮。不管怎么说,新粮可以多储一些时日。
但坤叔想得再周到,稻子还得年年储下去,储粮的最后限期还有二十年,怎么得了啊?说不定会虫蛀,说不定会发霉,而坤叔似乎从不在乎。
“为什么要想那些没用的事?反正我只有九年阳寿了。”每遇别人提出异议,坤叔就是那张土地公公一样的笑脸,又是反问又是自我安慰。
大概,这就是坤叔希望傻儿子早点“回老家”的原因。
坤叔说,人的阳世日子肯定是阎王爷帮你定好了的。有一回,两个傻儿子捧着几只毛都没长出来的死老鼠儿,争先恐后往嘴里塞,咬不动就整个吞,像鸭子吞青蛙。坤叔担心那是毒死的老鼠,因为他常年在粮仓附近放鼠药。坤叔发现后本想跑去抽他们几棍子,但刚拿棍子,两兄弟拔腿就跑,比山猋还快。死老鼠转眼也一个不剩。
“吃吧吃吧,你们早死早托生!”
坤叔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时候,已经只剩下一肚子兴奋:“你说怪不怪?想起来我就作呕,那几天看见他们我就吃不下饭,那只大黑猫吃了只死老鼠都把性命弄丢了,可他们卵事都没有。看来,阎王定你五更死,三更四更也死不成。”
(节选自短篇小说《七个老人八颗牙》,原载于《湖南文学》2014年12期头条)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