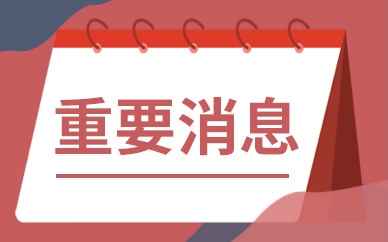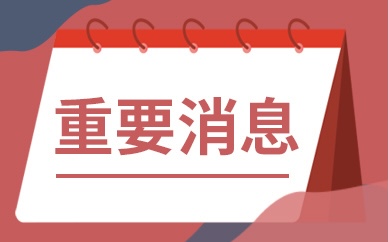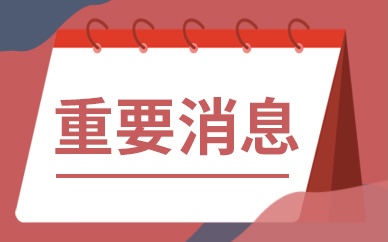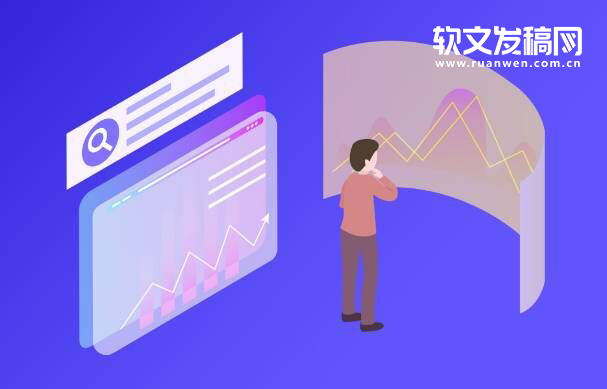在15世纪,法国有一位大主教写信给当时的国王说,“如果是为了国家的和公共的利益,我们确实不该拘泥于税负,但是我们需要征税方给予解释”。就是说,统治者要向被统治者征税,不能只用一句“是现实需要”或者“为了国家利益”作借口就可以打发,而必须给出理由,说明现在征税是正当的。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在西欧的封建时代,农民耕种领主土地要交纳地租,这个从私经济出发的封建义务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无需什么证明。可是,国王或者领主要求民众缴税却是在封建义务之外的,而要工商业从业者缴税就更是在封建义务之外,因为他们并没有从领主那里获得土地。如果统治者不能说明征税的理由,并由此得到纳税人一定程度的同意,那就意味着纳税人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而没有产权的一定保障,也就不可能有经济活动特别是工商业活动的发展,最终带来的只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利益上双输。
在全球视野中,西欧之所以率先走向现代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它能按照正当理由征税并获得了纳税人的谅解,私人财产权由此得到保障,经济剩余有所积累,在此基础上兴起相对富裕的农民与市民,经济力量增强的民众话语权提高,国家权力也因税收增长而增强。
提供征税的理由,实质上就是设法论证税收的正当性。这样的论证,既可能由统治者作为征税一方提出,也有可能由被统治者作为纳税人一方提出。征税的理由及其发展,在现实中起到了驯化国家的作用。就是说,主张并遵循征税的理由,让现实中逐渐发展的税收国家变得越来越为人所接受,由此一过程进一步地诞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国家。
征税理由的中世纪论证:公共需要
在中世纪,西欧国家发展的基础主要是当时的封建制度,因而在那样的制度下封建契约关系就成为论证征税理由的起点。这样的契约关系,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一个方面是,政治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私人性质的。就是说,在封建关系中,国王和各封建主的权力来源是相同的,都来源于土地财产;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现代国家中上下级权力隶属关系,而是私人与私人的关系。
另一个方面是,领主与附庸、自由民之间的关系是“契约”性质的,以相互负责(你给我庇护,我为你效忠)为前提,整个国家是一个松散的“契约”性质的社会有机体。
对于国王而言,自领地外获得的财政收入,至少一开始主要是基于封君封臣关系而得到的武士精英无偿提供的有限期军役服务。不过,由于客观上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技术的变化,主观上无偿军役提供者的意愿不足等原因,由国王临时征召、骑士亲身短期服务的军事制度慢慢衰落,国王越来越多地将军事义务转化为骑士阶层的纳税义务(即缴纳免役钱或者说盾牌钱)。用今天的眼光看,国王依托军役服务或盾牌钱获取收入,形式上有点像税收,但在性质上却具有私人性,是基于土地财产关系或自愿交换获得的,而不是依据公权力获得的。
除了根据军役制度获得收入外,封建制度还支持在军事紧急需要或确有必要时,封臣有义务向封君提供财政帮助。这种紧急需要或确有必要等理由,事实上构成了后世税收发展的前提。当然,国王提出的征税理由要能被算作“必要”,需要封臣的认可。确有必要的理由早期主要是军事上的“必要”,即王国正面临军事上的紧急状态。比如正处于外敌入侵的危险中,此时所有的成员都有责任来帮助国王。
不过至少在一开始,普遍的看法却是,军事必要是国王的个人需要,应由国王承担军事所需的费用(当然封臣还是要提供有限期军事服役的)。直到后来公众才慢慢承认,外敌入侵这样的紧急事件,确实构成军事必要,而且是所有人的共同需要,它可以算作征税的“必要”。比如,在1207年英国约翰王向各地发布的税收征收令中,把“保卫我们的王国”称作所有人的共同需要。到英王爱德华一世时期(1272—1307),“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含义,已等同于国家的共同危险(即外敌的威胁),战争成为征税的“必要”理由,发动战争或进行防御,等同于维护共同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国王才屡次召开等级会议,在会上请求各等级缴税帮助国王。
除了英国外,欧洲大陆的征税正当性论证同样经历了类似的理论发展。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的下述说明,反映了那个时代学者的认识:“当君主没有足够的资源反对敌人的攻击时……公民为了促进共同利益而作出必要的贡献是公平的。因此,一个为了王国利益而战斗的国王能够通过正常的税收形式调集全国的资源,当这样还不够时,国王可以对臣民加以特别的负担”。
不仅贵族与自由民因战争原因需要缴纳税收,教会也被迫同意为此缴税。1197年,罗马教皇召集的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承认,在世俗国家紧急需要时,教士应缴纳世俗税收,因为这种需要不是来源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来自对国家安全的共同利益的威胁,所以统治者有权从他的人民那里取得支持,包括财政协助,即缴纳税收。
由于军事上的“共同利益”标准逐渐成为征税正当性的共识,于是,贵族和自由民在等级会议上,就会以“共同需要”为标准来评判国王的税收需要,驯化国王的行为。
1254年,英王亨利三世为了给王子购买西西里王位而要求贵族缴税,而贵族们纷纷表示,购买王位不是王国的共同利益,而是国王的个人利益。随着对共同利益的理解,从军事领域逐渐向其他领域扩展,像道路维护、港口疏浚等,都逐渐被纳入共同利益的范围。君主们也乐于扩大解释共同利益的含义,以扩张自己的权力。
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英国在每一个征税法案之前都会加上一个导言,以说明给国王授征税权的必要性(即共同利益的需要),以便赢得议会的支持。到16世纪中期,英国王室要求民众提供资金的理由,已不再限于军事需要,而经常性地扩大到为了好政府而支付的一般成本。伊丽莎白一世1601年“金色演讲”指出,君主有一种神圣职责,要保护王国免受“危险、不名誉、耻辱、暴政和压迫”,它们既来自王国内部,也来自王国外部。可见,此时对税收必要性的说明,已超出了战争这个过去几乎唯一的公共需要。
12世纪开始逐渐复兴的罗马法,也为此一时期西欧国王扩大征税范围、增加税收收入提供了理论依据,国王代表着公共权威(而不仅仅是以私人面貌出现的领主)和公共利益,这在理念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时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虽然国王有个人的利益和来源于私权(土地分封)的权威,但其主要权威来源于或者应该来自王国的公共需要,即保卫王国、满足公共利益,也因此可以取得臣民的支持并从臣民那里获得财政帮助。这种从公共需要与公共权威方面来论证征税正当性,在此时实质性地跟论证西欧国家公共性联系在一起。
社会契约论:作为压倒性论证方式的兴起
向民众的私人财产征税为什么是正当的?封建时代的论述主要集中于论证它是为了帮助国王完成保卫王国和其他公共责任。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税收已不再局限于临时性地帮助本应自营其生的国王,而成为经常性、大规模和主要的收入形式。
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而言,以下有关税收国家的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要服从国家以至于要为它履行必要的职能去纳税?我们应该服从怎样的国家?或者说,怎样的国家才是正义的以至于我们有服从的义务?在16-18世纪这一近代早期,曾有不同学者分别从神学(如君权神授理论)、生物学(如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上篇所批评的菲尔麦的父权论)等角度加以论证,而社会契约理论在所有的论证中显然占据着压倒性地位。
大致说来,社会契约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它用契约来证明国家或者说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并以此对政治权威施加一定的限制;政治义务(包括纳税义务在内)并非天生的,而是契约的结果。换言之,为什么要服从政治权威,为什么要承担纳税义务呢?在中世纪,思想界早已达成这样的普遍性认识,“一项义务要具有真正的约束力,就必须由受约束的各方当事人自由地加以承担……归根到底,义务是不能用武力强设的,而始终是自我设定的”。因此,为什么要承担纳税义务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或者应该是,你在曾经自己设定的契约中同意过服从权威、缴纳税收,是你自愿选择的结果。
社会契约论之所以在近代早期能够成为压倒性的论证征税正当性的理论,除了前面说到的封建社会的契约因素外,还有基督宗教和罗马法等历史原因。不过,以下两个现实的契机也不容忽视。
一个契机是越来越商业化的环境,即12世纪城市复兴和商业发展以来,西方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契约的安排。“一个愈来愈以自由买卖契约为基础而安排其经济事务的社会,愈来愈以自由契约的眼光来观察它与国家的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另一个契机是英国在16-17世纪的政治实践,如1567年新教贵族强迫苏格兰女王玛丽退位、光荣革命发生后英国下院宣布废黜国王詹姆斯二世。在此过程中,都大量使用了社会契约论的语言,以至于社会契约已成为政治意识的一种常态。
霍布斯在征税正当性问题上的论证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把论证国家的哲学基础与论述征税正当性紧紧结合在一起。在霍布斯看来,国家拥有征税权非常重要,君主必须拥有集结军队并且征税供养军队的权力。在国家权力中,征税权甚至是最为重要的。
他在强调征税的必要性(即需要供养承担保护职能的司法部门与军队)时,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但他在主权者这个概念中,则加入了新时代的特征,即运用了社会契约的语言。用霍布斯的原话说,主权者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显然,这样订立的信约,就是社会契约。
霍布斯以孤立的、个体的人作为研究的起点,认为这样的人具有恶的本性(自私自利、残暴好斗、趋利避害),受自己内心无止境的欲望所驱使,同时还具有理性。在他看来,政治社会的建立就必须以这样的人性为基础,以满足人的欲望为目的。
在如此人性的基础上,霍布斯将缺乏公共权力后盾、普遍存在着孤立自私的个人这一状态,称为自然状态。在没有公共权力的情况下,人性的自私与争斗无限制膨胀,带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可人们对于自然状态中普遍存在的死亡状态感到恐惧,于是彼此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利,放弃的权利被授予一人或由多人组成的一个集体,大家都服从这个人或这个集体所代表的人格(即主权者),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是国家。
在霍布斯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制度是君主制,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这样一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能够最和谐地融为一体(即汇聚在君主身上),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内乱、结束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的国家哲学基础上,霍布斯对税收的本质给予了清晰的说明,并因此形成对征税理由的论证。他说,税收是一种通过供养国家来供养民众的“营养”,这种营养可能是国家提供的某种服务,也可能是通过国家转移的物资。他重点强调税收应该发挥的功能是保障安全,另外他也注意到税收所应承担的福利职能。
霍布斯运用他精心构建的社会契约理论,在征税正当性论证上,至少完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转折。
第一,从中世纪借助于封建惯例的论证,转向具有革命性的构建新社会或新国家的理论,强调征税权必须符合签订社会契约时的目的。
第二,从古典政治哲学中整体主义的目的论(即只有符合整体目的的政治才是正义的),转向新时代个体主义的政治目的论(即只有以实现个体权利为目的才是正当的),强调征税权必须有利于个体的安全与福利。
洛克对现代国家及其征税权正当性论证的完成
相对于霍布斯来说,洛克所表达的理论是一种很容易了解的、平凡的哲学,具有“普通人的理性”,加上他不同意霍布斯对君主专制的主张,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阅读和欣赏,并取得了更大的现实影响力。
在洛克看来,包括征税权在内的政治权力,其正当性的依据何在呢?洛克的回答与霍布斯相似之处在于,二人都不认为它来自上帝的赏赐,而主张它来自被统治者基于自由意志的同意。洛克说,是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组成社会和设立政府,因而个人是第一位的,是本源和目的,社会和国家是第二位的,是派生的和手段。
不过,洛克运用了自己的一些概念,构建了不同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成为现代政治的常识话语。到了后世,政治上即使不使用“社会契约”这样明确的字眼,但精神实质与话语体系也与洛克具有共通性。
洛克显然不同意霍布斯基于人性恶而将自然状态等同于战争状态的观点。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中,人类处于自由、平等、和平的状态,人不必服从于任何他人的意志,只需要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但由于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中不存在拥有权力的共同裁判者,在有人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时,缺少明确的成文法作为判断是非、仲裁纠纷的共同尺度,也缺少一个依法办事的共同裁判者,缺乏权力来支持公正的判决,使之得到执行。
于是,为了避免在自然状态中的不便,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通过以下两步契约形成可以征税的国家:首先,经所有人的一致同意,人与人相互之间签订契约组成一个政治社会,人们放弃自然法的裁判权和执行权,把它交给社会;然后,再由政治社会中的成员,依多数原则,成立一个服务于社会的信托机构即政府(统治者拥有最高统治权,拥有人们可以向其申诉的裁判权力),社会向政府授权来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政府为履行职责而有权征税。
在这样的国家哲学基础上,洛克认为,税收在本质上是私人财产权的一种让渡,而私人财产权先于政治社会、先于政府、更先于征税机关而存在。税收是用来保护私人财产权的经费,其自身是私人财产的一部分;政府并没有自己的财产(作为私人的国王有自己的财产),其本质只是一组权力(仅限于用来保护每一个人及其财产),而这种权力也是派生性的,无论是立法权和行政权,都只不过是每个人把他的天赋权力或自然权利“让渡给社会”而形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征税权是正当的?洛克认为,首先,征税的目的必须合法,即税收供养的国家必须因保护财产权(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而产生,并为此目的而运行;其次,一定要有纳税人的同意,而这种同意由议会来表达,即由议会决定征税与用税。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代议民主制不断地巩固并顺利地向新国家类型转型,对此洛克的理论奠定了比较可靠的思想基础。18世纪的英国,正是在以洛克为代表的众多思想家的影响下、在代议民主制下诸多国务活动者的努力下,于现实中逐渐地巩固了现代国家制度,在财政上表现为税收国家的逐渐成型。众所周知,洛克的理论还为美国独立建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结语
本文是要说明,在西方税收国家的兴起过程中,征税的理由是如何发展的。西欧在9-10世纪兴起的独特的封建制度,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保障基础和现代税收兴起的来源,它的契约性质还为有关各方提供了征税的理由。
而在近代早期(16-17世纪),学者们发展出社会契约论来承接封建契约关系下的征税理由。
其中,霍布斯与洛克基于前人的理论与英国的经验,建构起比较完善的社会契约论来表达以下观点:国家的正义与征税的理由来自民众自由的同意;个人是本源和目的,而社会和国家是派生等等。但二人从不同的自然状态起点出发,分别得出了支持专制君主制度(为保护个人安全)和议会民主政治(为保护生命、自由与财产)的不同结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洛克那个时代,所谓的民众是相对抽象的,并不指人人或所有人。那个时代的国家,并不掌握所有人的姓名,甚至连确切的民众数量与分布状况都搞不清楚。参与国家管理的,只有部分贵族或者精英人士,在地方层次上充当陪审员、充当民兵的普通人数量很少。在那时,甚至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纳税,提供主要财政收入的合法税种仍是传统的直接税(各等级依其地产而纳税),穷人按惯例不需要纳税。
那时的思想家,普遍地持有一种贵族理性主义的观点:只有少数精英才拥有智慧去发现什么东西对人民有利,普通人并没有这样的智慧,也不可能对人类生活的重要领域做出贡献。这样一种对征税理由的论证,可以称为“为民征税”。在后来的卢梭等思想家看来,这么做还远远不够,不仅要为民征税,而且必须“由民征税”,即征税与用税的权力始终控制在民众手中,才构成征税的真正理由。
(作者刘守刚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著有《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国家的财政面相》《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财政中国三千年》等,主编“财政政治学译丛”“财政政治学文丛”“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等三套丛书,并在得到App上开设音频课程“中华帝国财政30讲”。)
关键词: